[摘要]對于部分大型汽車集團而言,單靠新能源汽車來降低油耗水平同樣面臨可持續發展的難題。
近日,工信部的汽車燃油消耗量網站公布了我國去年12月的新車油耗通告,數據顯示,2017年12月,國產狹義乘用車(汽油車)油耗是國四階段油耗限值的128%,相對上一年同期的134%,略有降低,但從全年的油耗平均水平來看,2017年沒有呈現明顯下降趨勢。這與此前能源與交通創新中心發布的《中國乘用車燃料消耗量發展年度報告2017》(以下簡稱《報告》)結果一致。
以絕對值來看,如果不計入新能源汽車的核算數據,2016年我國整體油耗下降幅度為1.7%,與2006年~2016年的年均降幅相同,車企傳統燃油車的油耗水平并未明顯改善,沒有達到每年的油耗降低目標。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么?《乘用車企業平均燃料消耗量與新能源汽車積分并行管理辦法》(以下簡稱“雙積分”政策)對車企降低油耗是否有負面作用?車企究竟該如何正確應對日益嚴格的油耗法規?記者采訪了行業和車企相關人士,對上述問題進行了解答。
法規加嚴 油耗降幅“原地踏步”
據了解,我國2016年開始實行的第四階段油耗標準,規劃從2015年到2020年生產乘用車的平均油耗目標分別為百公里6.9升、6.7升、6.4升、6升、5.5升和5升,下降幅度不斷增大。
據工信部統計,2015年,我國乘用車行業平均油耗水平為7.04升/百公里,2016年下降至6.56升/百公里,降幅達到6.4%,但不得不提的是,NEV(新能源汽車)核算為其貢獻了0.32升/百公里的降耗數值,而通過傳統燃油汽車節能技術應用僅貢獻了0.16升/百公里的油耗下降。
對此,能源與交通創新中心的專家認為,車輛重型化和大型化的趨勢已成為乘用車降低燃料消耗的最大障礙,這與近年來SUV和MPV市場份額的擴張密不可分。數據顯示,從2009年至2016年,我國國產車的整備質量不斷增加,增幅高達13%,共計增重163千克。
“一直以來,汽車企業對油耗法規的產品規劃有錯誤認識。”某汽車企業工程師張平(化名)告訴記者,考慮到傳統燃油汽車節能技術的成本,車企更愿意通過生產新能源汽車來拉低平均油耗,傳統節能降耗技術的應用較少。
車企在技術路線上走彎路
基于此,能源與交通創新中心在《報告》中提出,新能源汽車的高倍優惠核算與“雙積分”激勵機制,增加了企業油耗達標的靈活度,也可能會驅使企業忽視對節能技術開發的投入及應用,轉而依賴于生產NEV或者入股NEV車企來實現合規。《報告》以某車企為例,在NEV不計入核算時,平均油耗高達9.76升/百公里,CAFC(乘用車企業平均燃料消耗量核算辦法)實際值與目標值的比值為176%,但加入NEV核算后,上述兩個數字立刻降至4.71升/百公里和84.4%。
但如果因此將板子打在“雙積分”政策上同樣有失妥當。在“雙積分”政策中,新能源汽車積分在核算時的放大倍數呈逐年降低態勢,2016年~2017年為5倍,2018年和2019年降低至3倍。張平透露,在目前新能源汽車銷量仍待提升的現實面前,汽車企業已逐漸認識到單靠生產新能源汽車難以滿足日益嚴苛的油耗法規,傳統節能技術的應用已被提上日程,例如車企研發部門已開始部署并開展下一代發動機的開發工作。
不過,張平指出,當前“雙積分”政策對未達標企業的懲罰效果還未顯現,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車企在技術路線上走了“彎路”。能源與交通創新中心專家則建議,把對不達標企業采取的通報、暫停產品公告不受理等行政處罰手段轉化為經濟懲罰機制,例如建立“懲罰基金”,用于獎勵先進發動機技術的研發與應用。
只靠新能源汽車不可取
對于某些還未開展新能源汽車布局的汽車企業來說,單靠傳統的節能技術能否實現2020年5升/百公里的油耗要求?張平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之一在于成本問題,以48V系統為例,在A級轎車和微車上搭載48V混動系統后,將降低10%的油耗,但相對的,整車成本也將上升4000元左右;原因之二是不同的節能技術疊加應用后,對產品的油耗降低影響并不是簡單的“1+1=2”的關系。
對于部分大型汽車集團而言,單靠新能源汽車來降低油耗水平同樣面臨可持續發展的難題。在張平看來,就目前的電池技術水平來說,新能源汽車的大規模普及和應用受到地域限制,面臨環境適應性難題,尤其在寒冷地區,新能源汽車的銷量在短期內還難以超越傳統燃油汽車,因此企業不得不放棄只靠NEV的這條路。
轉載請注明出處。
1.本站遵循行業規范,任何轉載的稿件都會明確標注作者和來源;2.本站的原創文章,請轉載時務必注明文章作者和來源,不尊重原創的行為我們將追究責任;3.作者投稿可能會經我們編輯修改或補充。




 熱點推薦
熱點推薦
 精選導讀
精選導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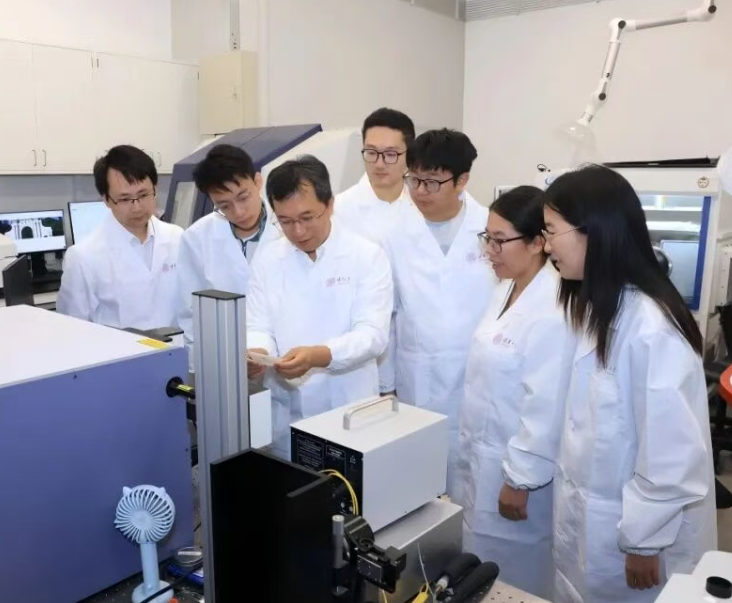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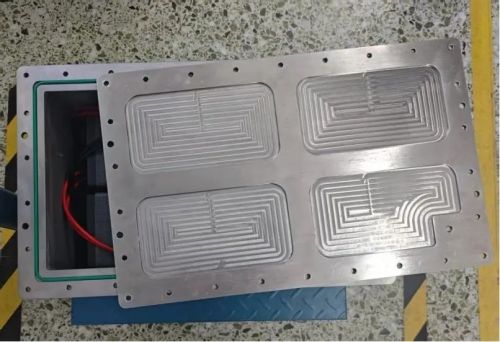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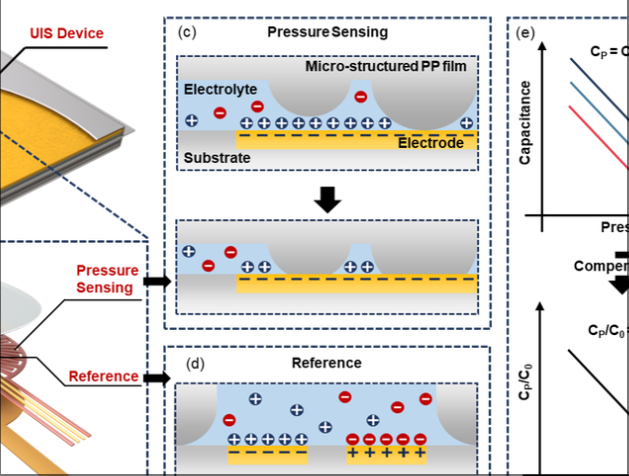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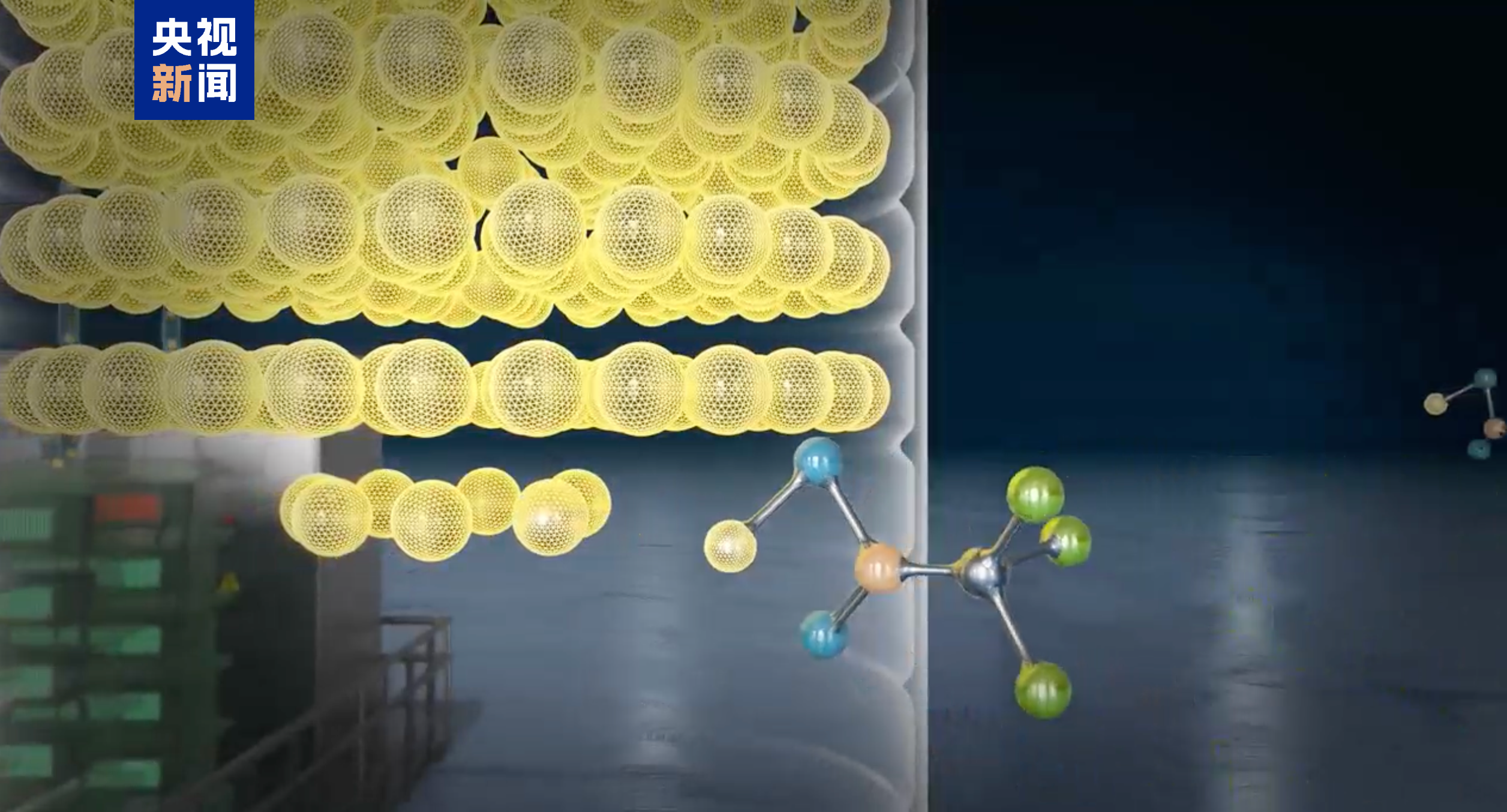


 關注我們
關注我們